每天上班路过营山县城十字口前的大南街,目光总会落在那间挂着“中国邮政”招牌的门市上。如今这里是快递收发点,门市内一角散装白酒的塑料膜随风晃,恍惚间竟和记忆里集邮门市的风铃重叠。在我心里,这地方永远是1998年春天的模样 —— 营山首个集邮门市,我踮脚看邮票的秘密基地,藏着整个童年的邮事。 1997年我上小学二年级,电影频道难得播了次《邮缘》,丁大森对邮票的痴迷让我记了好久。我开始翻家里旧信封,用指甲刮掉邮票残胶:《万里长城》砖缝细得能藏蚂蚁;《水浒传》史进习武邮票最让我着迷 —— 王进站旁指导,史进握棍的模样清晰,我找竹竿模仿,蹭到篱笆都没察觉。那股认真劲儿,像极了当年看电影《少林寺》后执着练打沙包的孩子。那段时间,我最宝贝1993-6《第一届东亚运动会》邮票。两枚横双连连印,中间是上海体育馆,右侧吉祥物小鸡“东东”举着小火炬,黄色绒毛、圆眼睛,比书中小动物还可爱。一次折了邮票角,我急得哭,妈妈用字典压了好几天才恢复。双休日下午,我在书架摸到妈妈的集邮册 —— 封面印着故宫九龙壁,角落缀着枚大清大龙邮票图案。妈妈翻给我看:“从南充财贸校实习到营山县煤建公司,同事和亲友的信封我都留着揭邮票。” 她指着一张8分万里长城:“实习时寄信全靠它,那时平信邮资就8分。” 她揭邮票格外小心,粘得紧就用剪刀贴边剪,生怕碰坏图案。那晚,我把妈妈的集邮册和自己的东亚运动会邮票放枕头边,翻到“东东”那页折了角才睡。买邮票要去模范街邮电局营业大厅 —— 现在是中国电信营业厅,当时刚改造,瓦房换成门市,没有如今的手机店,多是生活气小店:营业大厅出门左拐的侧面,是“巫二娃餐馆”,饭点时总能飘出炒菜香;大厅对面有卖猪饲料的门市,旁边挨着音响店、县种子公司门市;街角的打印复印部能租 VCD,我在那儿租过《玩具总动员》;街上还有好几家服装店、一家化妆品店,“司长河诊所” 的红招牌老远就能看见。我攥着妈妈给的零花钱往邮电局跑,路过左拐侧面的 “巫二娃餐馆” 时,总忍不住闻闻菜香,直到走到营业厅门口,才收敛心思趴在玻璃门上望。手心总把钱攥得汗湿,纸币边角都软塌塌的,柜台阿姨说:“只有寄信用的邮票,纪念票要订年册,一百多到两百块。” 我蔫了 ——年册里好多邮票我不感兴趣,只好每次路过都趴在玻璃门上望一眼,腿蹲得发麻才走。1998年初春双休日,我路过大南街,突然看见“中国邮政”黄色大字 —— 绿色招牌漆色新鲜,玻璃门贴着“新邮到货”海报。我趴在玻璃上看,柜台里邮票像过年的水果糖,赶紧跑回家拉妈妈来。柜台锃亮,能照见我短头发,里面套票、小型张整齐,还有印着 “1998.03.15”的首日封。我踮脚点着 1998-3《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》邮票,又盯着《岭南庭院》花窗:“跟外婆家堂屋的好像。” 妈妈帮我买了《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》套票和《傣族建筑》特种票。那年五一,妈妈在南充加班,带我去古玩市场邮票摊,翻了好几个邮册,选了本浅红色空白邮册给我 —— 封面印着《三国演义》(第一组)小型张,刘备、关羽、张飞“桃园三结义”的纹路、桃树都清晰。“以后邮票有家住了,别像我当年夹书里揉皱。” 我用镊子把东亚运动会、傣族建筑邮票小心夹进去,连镊子都在衣角擦了擦。这浅红色邮册成了我的宝贝。每天放学,我从垫着旧棉布的抽屉拿出来,用镊子夹邮票,不敢碰图案。看《傣族建筑》邮票,对着课本知道竹楼吊脚防潮;看《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》邮票,翻爸爸买的《少儿百科全书》,不认识的字查字典;连《岭南庭院》的缠枝莲纹样,我都能跟同学说“这代表吉祥”。有时妈妈带我去集邮门市,我蹲在柜台边听:罗大爷拿放大镜指集邮册内的《奔马》小型张:“要放避光处,我家那套放窗台半年就褪色了。” 阿姨翻到集邮册插页内的首日封叹气:“戳记碰水就花,我儿子洒了水,吸干还留印子。” 戴眼镜的叔叔举着《三国演义》(第五组)套票和小型张:“这套可能升值,多买了给儿子当纪念。”我盯着他手里的(第五组)小型张,清楚地看出和我邮册封面上(第一组)“桃园三结义” 图案不一样,却也看得入了神。这些细碎的知识点,我都记在心里,至今记忆犹新。可热闹只持续了一年。1999年初,新城路新邮政营业厅建成。元旦后双休日,我约同学去看他爸爸珍藏多年邮册,路过老集邮门市,卷帘门贴着白色搬迁通知,纸边被风吹卷。我摸了摸通知,心里空落落的,全程走神,满脑子都是门市看邮票的模样,还有我邮册封面上的“桃园三结义”。如今大南街的门市早换了模样,快递车来来往往,取件人抱怨 “要等好久”,缴电费的居民跟营业员唠 “电费贵了”,墙角的散装白酒偶尔有老人买半斤,说 “比瓶装酒够劲”。只有我路过时会多望一眼 —— 仿佛还能看见当年踮脚趴玻璃的自己,短头发被风吹得微微晃动;看见妈妈笑着给我买邮票的模样,指尖轻轻捏着邮票边缘,生怕碰坏一点;也想起模范街旁的热闹景象:左拐侧面 “巫二娃餐馆” 的菜香、音响店的流行歌、租到《玩具总动员》VCD 的开心,还有“司长河诊所”那醒目的红色招牌。那些年攒下的邮票还在父母家书房内专门放邮票的柜子里面,浅红色邮册的封面有点泛黄,但《三国演义》(第一组)小型张的 “桃园三结义” 依旧清晰;《傣族建筑》的票角微微卷了边,是当年我不小心把邮册掉在地上弄的,现在每次看到,都能想起当时着急哭的样子;《第一届东亚运动会》的“东东”邮票依旧鲜亮,举着火炬的模样好像还透着劲儿;《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》的套票红色底色一点都没褪,就像我当年在《少儿百科全书》里读到的故事,永远清晰地记在心里。它们从来都不只是印着图案的纸片,是童年里关于等待的雀跃、发现的惊喜,是妈妈的陪伴与爱,更是模范街旁那些藏着生活滋味的小店共同编织的记忆。大南街的门市会变,时光会慢慢走,但藏在邮票里的童年,永远鲜活如初 —— 每次翻开那本浅红色邮册,我都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攥着零花钱、踮脚看邮票的小男孩,心里满是简单的欢喜。
文章不错,点个赞吧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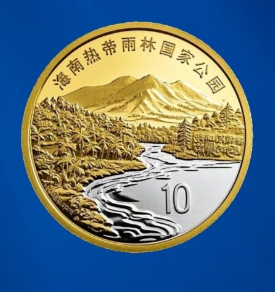






1